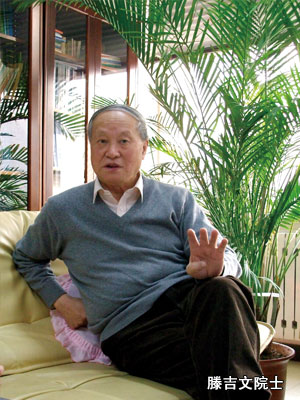
光阴荏苒,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悲痛逐渐远去,但留给我们的防震抗灾、灾后重建工作依然艰巨。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本刊记者就汶川地震研究及地震预测等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以期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汶川地震形成的原因,了解防震抗灾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这一科学领域在未来发展中的导向。
记者:滕院士,您好!汶川地震过去一年了,首先请您从科学角度谈一下汶川地震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滕吉文:汶川大地震的发生,确实令人震惊和悲痛,故应当成为我们在地震灾害的预测和防震、抗震征途上更加刻苦奋进的动力,也促使所有地震科技工作者在地震预测的艰难征途上刻苦奋进,不断去寻找切入点,深入研究,不断逼近地震预测的“彼岸”。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不断深化认识地震成因,进而在预测的基础上,强化防震、抗震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记者: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您对本次地震的“孕育”、发生和发展过程做了大量研究,那么此次地震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滕吉文:做了大量工作谈不上,但作为一个地球物理学家,又是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我是在努力,从内心确实想为这次大地震尽自己的薄力。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不同于一般的地震,它是发生在一条地质构造和GPS变形测量近期并不显著活动(相对于短、临地震预测)的龙门山构造带上,造成了以汶川县映秀镇为中心及其周围地域的严重破坏和人员的重大伤亡。然而强烈地震发生前却未见确切的能判别与这次大地震有因果关系的征兆或浅表层的异常活动,即浅层过程与地震发生的深层过程并不匹配。为此就迫使我们必须对这次地震的“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深层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初步研究表明:第一,在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陆—陆碰撞、挤压作用下,喜马拉雅造山带东构造结向NNE方向顶挤、楔入青藏高原东北缘,迫使高原东部物质向东流展,在受到以龙门山为西北边缘的四川盆地阻隔下,一部分物质则转而向东南侧向运移;第二,龙门山地带在地形上高差达3500±500m左右,地壳厚度在龙门山西北部为60±5km左右,四川盆地为40±5km左右,而龙门山地带则是与其西北、东南两侧相比,其变化幅度可达15~20km的突变地域,且向东南逐渐整体减薄和抬升,即为应力作用的耦合地带;第三,中、下地壳和地幔盖层物质以地壳低速层、低阻层(深20~25km)为第一滑移面,以上地幔软流层顶面为第二滑移面,且在四川盆地深部“刚性”物质阻隔下,以高角度在龙门山断裂系和四川盆地的耦合地带向上运移(或称逆冲),且在龙门山地表三条断裂构成的断裂系向下延伸到15±5km左右深处汇聚,上、下运移的二者强烈碰撞、挤压,震源介质强烈破裂,且在物质与能量的强烈交换下,应力得到释放,故形成了这次大地震。
记者:那么请问滕院士,对汶川大地震的研究取得了哪些创新成果?其成果对于未来的地震预测研究有何积极作用?
滕吉文: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的深入研究,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汶川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过程不是由于地表断裂活动和表皮推覆造成的,而是由于地壳深部物质运移的原因造成的。为此,对地震的研究,特别是强烈地震的研究,必须集中于在力源作用下震源区和其周边地带物质的重新分异、调整和深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且必须十分重视其深层物理—力学过程和动力学响应。
因此,越过地平线去“抚摸”地震震源区及其周边地域介质与结构的“脉搏”,把握其介质的微破裂和“破裂链”的逐步形成与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介质和结构的深部环境,以逐步向地震发生时间和地点的短、临预测逼近乃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因为地震的“孕育”、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震源体积,真正的发震断裂是龙门山断裂系三条断裂以不同角度西倾、并向深部汇聚、与深部下地壳和上地幔盖层物质向上运动,这二者在15±5km处强烈碰撞而构成的这条断裂带。显然将投影在地表的震中位置与某条断裂相近而将这条相近的断裂视为发震断裂是欠妥的。这就是说发震断裂应是深部15±5km处的这条汇聚断裂带。因此不论是主震,还是4万多次余震的震源深度均为15±5km。
记者:就目前而言,地震预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呢?
滕吉文:地震学家把地震预测定义为:同时给出未来地震发生的位置、大小、时间和概率4种参数,每种参数的误差均应小于或等于一定的范围。地震预测通常分为长期预测、中期预测、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在我国,以数年至10年、20年为长期;1年至数年为中期;数月为短期;数日至十几日为临震。这就是说地震预测必须给出时间、地点和大小。例如,若有人提出在中国大陆和临近海域近年将会发生7级或大于7级的强烈地震,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可是政府部门很难发出地震预报。
就目前来看,地震预测既是一个亟待攻克的世界性难题,又是一个亟待实施的防震抗灾工程。地震的“孕育”、发生和发展受到众多要素的制约,而且每一次地震都有其本身的特点和深层动力过程。为此,给地震的预测带来了众多的未知数。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在防震抗灾工作上的确付出了艰苦劳动,曾成功预报了海城强烈地震,在世界地震预测工作中走在了前列。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经验性,而非物理预测。
记者:我们都知道地震预测很难,它主要难在哪里呢?请滕院士给广大读者详细介绍一下有关知识。
滕吉文: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我国(包括台湾岛)曾发生了多次强烈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75年海城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灾害一次次发生,但是基于地震预测的艰难,人类尚无力阻挡。尽管地震预测目前已有一些理论模型,但是这与地震发生的实际情况还有很大差距。地震预测的困难,在于至今人们尚不能真正厘定不同类型、不同地域所发生强烈地震的规律或标志,尚难于“抚摸”地震震源处介质与结构的“脉搏”,即难于早期知道地震发生前的破裂过程及其邻域的状态,并且对其物理—力学过程和动力学响应几乎一无所知。地震预测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入地难,即深入到地球震源深处很难。迄今最深的钻井是前苏联科拉半岛的超深钻井,达12.2公里,这与地球平均半径6370公里相比还是很小的“表皮”,即还是不能直接对震源处的活动进行观测,而通过地球物理方法精确探测地震活动区的深部介质与结构环境及其介质与结构的属性,对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地点确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若能在强烈地震活动区布设深钻井,在井中放置高精度的仪器,以测量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深层破裂过程,确实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地震发生的周期是很长的,这就必须几年如一日,几十年如一日,乃至几百年如一日地坚持观测和采集数据,即连续地进行观测方能奏效。
二是大地震发生的周期很长,并非常常发生。大地震的复发时间比人的寿命、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长得多,限制了作为一门观测科学的地震学在对现象的观测和对经验规律的认识上的进展。迄今对大地震发生之前的前兆现象研究仍然处于对各个震例进行总结、分析和探索阶段,尚缺乏建立地震发生的理论所必需的切实可靠的经验规律,而经验规律的总结概括以及理论的建立验证却都由于大地震的发生(特别是重复再现是一种稀少的,即非频发事件)而在认识上和规律的厘定上受到很大限制。
三是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物理过程和动力机制的复杂性。强烈地震往往发生于极为复杂的深部介质和构造环境之中,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地震发生的过程是高度不均匀的、各向异性的和非线性的,它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深层动力过程。地震前兆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可能与地震震源区介质与构造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地震“孕育”过程的高度不均匀性、各向异性和非线性密切相关。
记者:地震预测如此困难,我们应该如何提高防震抗灾能力?如何提高地震预测能力?
滕吉文:在对地震预测的不断探索进程中,强化防震、抗灾乃当务之急。地震预测和防震、抗震必须并行,即实施“双轨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重大破坏和经济损失。实现地震预测的科学途径主要包括: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家的刻苦奋进;加强对地震及其前兆的判别、厘定、观测和真实规律的识别;坚持地震预测科学实验,即地震预测试验场和井下破裂效应的长期观测;加强强烈地震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深部精细介质和构造环境与深层动力过程的研究;多元可靠信息的集成和高层次的有机综合研究;加强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加强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