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2010-11
一生多磨难 天道常酬勤
本刊记者庞贝 杨波
2010年11月01日
在采访中,张承志为了阐述早临的灾难未必是祸,往往是福这一观点,娓娓道来一句司马氏名言让我们印象深刻:“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可以想见,在过去几十年的漫长人生旅途中,他就是以这种精神砥砺自己,才没有在逆境中败下阵来,终于以一己之力得偿夙愿,创立文物保藏学的理论体系。在体制之外,呼吸科学的自由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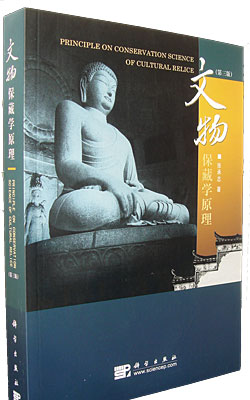
张承志著《文物保藏学原理》
理论保藏学新篇
我国是文明古国、文物大国,文物保护受到人们的重视。“保藏学”就是在这种背境中诞生的。笔者粗读了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物保藏学原理》这部60余万字的巨著,从字里行间可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发散性思维,在数、理、化及生物学领域、在众多工科领域纵横的踪迹,学科间的界限在这里变得非常模糊,跨学科研究的时代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保藏学”由“理论保藏学”和“技术保藏学”两部分构成。“理论保藏学”是研究环境因素、时间因素、残余应力因素对文物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的学科,因为文物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将发生四种形式的自然劣变:色变(褪色、变色、泛黄、失光)、形变、质变、破裂(脆性材料依赖于时间的重要行为,是应力腐蚀造成的开裂或断裂)。
2003年,《文物保藏学原理》第二版面世后,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选作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研究生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院系,多年来一直延用1999年第一版《保藏学原理》,作为外国来华留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该书的教学、科研价值得到了顶尖学府的认可,这是对张老研究成果的最好回报。在情报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参考书目中,保藏学亦有显赫位置,这说明张承志的理论具有国家级科研导向作用。该书的第三版被选作高校考研及教学用书,获得至高的荣誉。
“理论保藏学”的诞生,使文物保护这门古老的学问,由描述性学科转变为实验性学科,从而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独立新学科。文物、档案的各种细微劣变在书中都用方程量化。因此它在考古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的科研、教学及技术应用中起着重要作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估量。
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领域,由中国学者创立新学科是件大事,张承志教授恰好是在这一敏感领域创立了“理论保藏学”,显然这是一项不应被忽视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回顾学科发展史便可知道,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汇处、在工程技术领域,创立过多门新学科。但在自然科学基础应用理论领域,却很难找到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张承志研究员经历38年艰辛探索的‘理论保藏学’,则是个例外。该学科面世后很快就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考古等领域,迅速被最高学术阶层接受,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科技日报》2010.8.31)。“理论保藏学”经历了11年的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没有负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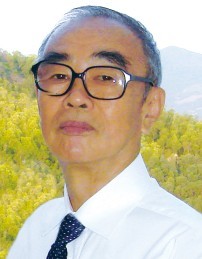
张承志先生
自由精神——体制外科学家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或许正是为了追求这种不被束缚的科学想象力,张承志虽然身处各种体制之中,却将思想时时游离于体制之外,上下求索,才将敏锐的思维触角转化成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成果。
他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绩斐然的科学家的人生经历,不仅验证了逆境对于人才成长的正面作用,而且也说明自由活跃的科学思想和科研环境对于创新的积极意义。

张书诚先生
张承志幼年丧父母,命运多舛,14岁还是文盲的他,遇到一位知识分子军官张书诚,这个人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张书诚虽然与他非亲非故,但是却认定这个年少早慧的孩子是个可造之材,于是上书上海华东局要求给这个少年上学的机会。华东局难于顾及此类小事,于是张书诚打报告要求复员回乡。张书诚此举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培养人材。这个报告被批准了,张承志从此有了上学的机会。
高中毕业时政审外调,张承志莫名其妙地背上了有台湾亲属的“恶名”,当时有这种关系考大学是很难的。他慎重地选报了政审比较宽松的北京林学院。该校绿化系生物物理专业果然大胆地录取了这位学子。绿化系是从清华大学合并到北京林学院的,教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且是五年制本科。这位年轻人首次品尝了因祸得福的味道。
大学毕业时,张承志本来可以分配到科学院,但又因有人从中作梗,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不但科学院去不成,其他单位也不敢接收他。无奈之下,张承志只好请求回乡种地,并因此事一病不起,住进了天坛医院。他的六位同学联名给学校写信,要求给张承志平反。经过调查,校方为其正名。北京市人事局大学科的负责人很同情这位受害者,因此给了他一个特权—由他自己挑选工作单位,他高兴地选中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二次因祸得福。
张承志分配到自然博物馆,无奈地接受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植物分类工作。他在工作中渐渐发现各种生物标本劣变严重,又听说1962年国家科委曾向中国科学院的两个研究所和自然博物馆下达过一个防止生物标本劣变的研究课题。三个单位联合攻关,最后不了了之。张承志带着忧谗畏讥的心情,提出独自重启这一课题的请求,于1972年得到室主任的批准。
申请课题获得批准,但申请购买试剂做实验时却被拒,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次张承志在帮助一位老先生打扫实验室时,捡拾到多瓶老人丢弃的过期试剂。这些试剂帮了他的大忙,让他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市科委领导五年后发现这一成果时大悦,当即决定将该成果报请参加市科学大会。这位命运坎坷的青年第三次因祸得福。
张承志未花一分钱完成了国家课题,引起市科委的重视,在随后的技术性研究中得到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与助手一起相继创建了两个出口产业,填补了国内3个产业的空白,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受到市科学大会的表彰,并获得了三次市级科技成果奖。
1980年张承志获悉文物界急切需要保藏学的理论支持,于是他把研究拓展到文物、档案界这个新领域,步入了自由探索的另一历程。
名不见经传的张承志因成功而招来了磨难,“三个通常”不停地捉弄他的命运。“所谓‘三个通常’,是指当年我的研究成果通常不被上报;上报我的成果时通常不写我的名字;评职称时通常让我评不上。这三点恰是科研人员的三大命脉。”(《今日科苑》2010年14期)。
为了应付这种状况,张承志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继续从事研究。“明修栈道”是指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用来创造经济效益;“暗渡陈仓”指利用技术转让费向单位换取时间的自由支配权,从事保藏学的理论研究。这样做虽能确保理论研究的安全,但却无法申报课题、无法申报成果,致使现在的成果成了无人过问的弃儿。
张承志通过“修栈道”,先后向单位提交了6次以上技术转让费,换得足够长的自由探索时间。当其无力再“修栈道”时,只好请求提前三年退休,回家“渡陈仓”。就这样,通过对原著修正、补充,《文物保藏学原理》总算修补完成,为了完成这本专著并得以出版,他卖掉了房子。到第三版面世时,已历时38年。
张承志的研究经历在科研史上相当奇特,他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野草,应逆境而生,应逆境而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通常”的磨难使这位古稀老人第四次因祸得福,在逆境中抢占了世界理论保藏学的制高点。
张承志历经磨难却一直没有倒下,除了源于他有一颗乐观奋进的心,还源于他一直着力保护着的、不被体制束缚、不被专业束缚的自由敏感的科学探索精神。
“人们将会永远记得,是一位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艰辛探索‘保藏学’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文物劣变的机理,破译了困惑人们的又一个难题”。(《科技日报》2010.8.31)
张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者、《花色之谜》译者、《文物保藏学原理》作者、《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入选者。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曾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凯撒国际教育集团亚洲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