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2010-10
跑好自己在科学接力赛中的一棒
本刊记者庞贝 陈硕
2010年10月01日

2010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做报告
地学人生——“跑好自己的一棒”
莫宣学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学生中走出的第25位院士,他的地学之路也走过了50多个年头。在过去的35年间,他累计有73个月在野外工作,其中70个月是在青藏高原和西南“三江”地区工作。
他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与岩石紧紧联系在一起。看似没有生命的岩石,在他的眼中是凝聚亿万年自然信息“密码”的“信使”,而他的地学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破解岩石身上的“密码”,进而探索地球深部及构造运动过程的秘密。
莫宣学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岩浆—构造—成矿’。也就是以岩浆作用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为基础,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地球动力学,就是将岩浆岩及其所携带的深源岩石包体当作探究地球深部的‘探针’和‘窗口’,以及大地构造事件的记录;二是成矿,就是研究岩浆作用与成矿作用的内在联系,寻求规律,服务于国家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在恩师池际尚院士的推荐下,1981年,莫宣学来到了池先生曾经工作过的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著名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跟随著名岩石学家卡麦克尔主攻岩浆热力学。当年,他完成了国际上第一个含Fe2O3多元硅酸盐熔体中主要组分偏摩尔体积及岩浆氧逸度对压力的依赖的实验。1982年,他与卡麦克尔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该成果的论文,首次提出了计算任意压力下岩浆氧逸度的公式、含Fe2O3熔体密度预测模型及不同类型岩浆的P-T-αSiO2-fO2关系图解,为建立岩浆演化综合热力学模型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岩浆成矿作用和行星演化研究有重要科学意义。美国的两份国家报告把该成果列为熔体热力学的重要新进展,该成果至今被各种国际著名杂志他引超过百余次。
莫宣学和他的研究团队一起,对青藏高原构造-岩浆作用进行了几十年长期系统的研究,在印度与亚洲大陆碰撞时限、青藏巨厚地壳的成因、青藏高原深部物质流动等重要科学前沿问题上做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取得了有国内外影响的成果。
他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服务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迫切需求,从“七五”计划开始,莫宣学及其研究团队就一直奋战在川滇藏“三江”特提斯成矿域,研究岩浆作用与成矿作用的关系,提出了“两大成矿系统、三大控矿要素”的理论概括,指出“三江”成矿是特提斯成矿系统和碰撞—后碰撞成矿系统叠加,受壳幔地球化学不均一性、特提斯事件、印度—亚洲碰撞事件三大要素控制,并指出具体的找矿方向,与地勘部门密切合作,为开拓国家级“三江”矿产资源新基地做出了贡献。

2005年组织西藏地质野外研讨会与美国等国部分专家在喜马拉雅合影
(左四为美国Depaolo院士、右四为IGCP430主席Flower教授、左二左三为潘桂棠莫宣学教授)
怎样理解“创新”
在讨论到怎样理解“创新”时,莫宣学院士说:“创新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在永无止境的科学接力赛中,不断做出不同于前人、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过去的新贡献,就是创新。树立这样的意识,就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美国人常说‘Do something new’,就是一个很形象的表述。”
“创新有大有小,做出大成果固然是创新,而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即使很小也是一项创新。很多有意义的小创新不断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就可能产生对经济、社会与科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大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的报告中对创新做了全面的阐述,将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以后的再创新三类。他提出了我国科技重点发展的八大领域,为全国人民和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创新的方向。”
“科学史证明,任何学科,当它与人类的当前和长远需要结合得最紧密的时候,也就是它突飞猛进的时候。相反,如果脱离了这种需要,它的发展就要减慢甚至停滞,所谓‘创新’也就失去了方向。我们今天讲创新,就是要为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而不是为个人名利去创新。”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谈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时,莫宣学说:“培养创新性人才,是我国教育的历史性、战略性任务。我没有能力去全面论述它。但作为一个老教师,我想向青年朋友们贡献以下意见。”
“第一,未来的创新型人才首先必须夯实基础,而坚实的基础、过硬的基本功,只有在长期艰苦的实践中才能炼成。不同学科,其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功的内涵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夯实基础,着力培养学生观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地质学来说,共同的基本功是野外观察与填图能力、野外和显微镜下认识岩石和矿石的能力。
观察是认识的基础。没有对实际材料的周密系统的观察和收集,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分析与综合。如果感性材料是东鳞西爪、残缺不全、片面扭曲的,那么据此所产生的结论就必定是不可信的。但是,要进行正确而有效的观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样观察一个地质对象(例如,一个造山带、一个岩体、一块岩石等等),有的人长久不得要领,而有的人却能迅速地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信息量最大、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从常人熟视无睹的‘普通’事实中找出可能产生新思想、新理论的苗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思维方法上、学识经验上和对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程度上的差距。记得有一位名家说过,一个科学家的水平不仅表现在他是否善于提出有价值的结论,而且首先表现在他是否善于进行有价值的观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有一种只热衷于理论、模式,轻视观察,尤其轻视野外地质工作的倾向,是很有害的。”
“第二,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必须有广阔的知识面。学科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来区分的。学科的形成与分工,本来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分工,把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各学科隔绝起来,那就走向了反面。特别在今天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当今科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任何自我封闭的学科都将是苍白无力、没有前途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邻、相关学科,尤其是基础学科与本专业学科的结合与渗透,常常能够给本学科研究以重要的启迪,甚至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新的学科方向与新的边缘学科。任何学科只有从其他学科的成就中不断吸取营养,才能有永远的活力。创造性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与科学家的天赋有关之外,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是否善于学习,善于用古今中外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是否有渊博的学识和对科学发展动向的透彻了解,是否勤于思考,只有知识渊博、思路开阔的人,才能具有对新苗头、新动向、新事物的高度敏感性。”
“第三,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思维和意识。创新性思维是科学家最宝贵的素质。进行科学创新,不仅要有对实际材料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而且需要有丰富的科学想象力和创新性思维。没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就不会有创新性的成果。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某一地区、某一研究对象虽然有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资料积累,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想象和创新性的思维,没有发挥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总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第四,未来的创新型人才,不要拒绝从小事做起。最近感觉到一些浮躁情绪,做事情只愿做‘大事’不愿做‘小事’,总想‘一夜成名’,做研究只愿做大项目不愿做小项目,以为研究地区和题目越大就越有国际影响,以为小地区的研究出不了大理论。其实,能否出有国际影响、世界影响的科学成果,关键不在于研究地区的大小,而在于研究的深度和创造性。只要研究得深,真正抓住了规律,揭示出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无论研究区域大小,都有产生重大理论创造的可能性;反之,即使研究地区覆盖全国、全球,也只能停留在对事物的外部(表面)联系的认识上。为什么毛主席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影响?为什么对格陵兰的一个小小的岩浆岩体的研究能够产生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岩浆演化理论?为什么对一些具体地区地质问题的研究能够产生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地质理论?就是这个道理。一切共性都寓于个性之中,没有对个性的深刻认识,就没有对共性的深刻揭示。浮躁情绪是科学的大敌,也是青年人成长的大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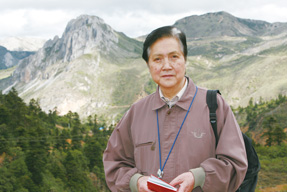
莫宣学院士在云南香格里拉县普朗铜矿
发展地学的机遇与挑战
谈到我国地学如何创新,莫宣学院士认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旗帜的新的地学革命的前夜,这对我国地学的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又是一个极为宝贵的机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失去了在以板块构造为旗帜的地学革命中发展我国地学的宝贵机遇,遭受了重大损失,落后了几十年,这次一定要抓住。只有这样,我国地学才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地球系统科学,就是将地球当作一个统一的大系统,研究地球整体运动的规律及各圈层间的相互作用;地球动力学及全球气候变化是它的两大主题;地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地球、开发资源、改善环境、减轻灾害。无疑,新的地学革命将是一场内容深刻、影响深远的革命。
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情况复杂多样,拥有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质“特产”,为我国地学工作者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进行理论创新的广阔天地与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青藏高原,不仅是举世无双的世界屋脊,也是世界上保存特提斯地质记录最完全的地区,此外,诸如巨大的高压—超高压带、东部岩石圈破坏、黄土高原,等等,都是我国特有的,但却具有全球意义。因此许多外国专家说,中国掌握着打开世界地质奥秘的金钥匙。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特有的地质地理条件,从中国地质地理特殊性的研究中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