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斗,我国著名动力机械工程和工程热物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2年生于上海,1950年入清华大学,1957年前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毕业,1962年在原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1990年被授予俄罗斯荣誉科学博士,1991年被选为国际高校科学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攀登计划”B项目首席专家、煤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主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
 邓小平接见倪维斗
邓小平接见倪维斗
1932年10月6日,倪维斗出生于上海一个工商世家。父亲倪家玺是著名的爱国工商界人士。父亲立身公正、热爱祖国的精神给倪维斗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他办实事、说实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和不赶潮流的性格。
1950年,意气风发的倪维斗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刚刚解放不久的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被选派到前苏联学习。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大批选派到前苏联的留学生,他们在北京饭店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铭记着党和国家的重托,19岁的倪维斗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前苏联最有名的工科大学莫斯科鲍曼高等工程学校学习。
由于时间仓促,留学前倪维斗除了会“我不知道”、“哪儿是厕所”等几句必要的句子外,对俄文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倪维斗回忆说:“是一位不懂中文的前苏联女教师教我们三个中国学生学俄文,那时一篇课文要念几十遍,念到顺嘴就说出来。”他说,有时同屋的前苏联人对他念课文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大叫“别念了!我都背出来了,你还在念哪!”那时这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们刻苦的学习态度和出类拔萃的成绩给前苏联的老师和同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倪维斗毕业时,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课程都得了5分。回忆起在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和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的学习生活,倪维斗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前苏联人民友好的情谊,让倪维斗有了“前苏联情结”。
留学5年半,为了给国家省钱,倪维斗他们没有回过一次国。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和买一些书之外,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花,同时还尽可能为祖国作些贡献。中国在前苏联开展览会,他们都报名当讲解员,大家还把当讲解员得到的报酬,即一块衣料换成现金上交给国家。在回国前,他把那几年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所带回国的只是几箱书。
倪维斗对那段黄金岁月充满了依恋。他说:“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我乐观、率真的性格和单纯的内心,也给我的科学知识、科研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没有一直留在前苏联呢?倪维斗说:“国家派我出来就是要我回来之后做些事,当时没有一丝一毫想过要留在前苏联”。倪维斗在回国之前,按照指示没有买任何中国所没有的前苏联商品回国。那时的倪维斗没有太多的选择,更没有太多的想法,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国后好好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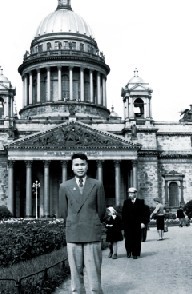 倪维斗在前苏联留学
倪维斗在前苏联留学
迷茫中的岁月蹉跎
1957年,倪维斗从前苏联学成回国。但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虽然踌躇满志地要为祖国作一些贡献,但基本上什么业务工作也没有机会去做。在1960年初至1962年底,他再次留苏,到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读研究生,并取得了副博士学位。
1962年回国后,正值年富力强的倪维斗在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当了一名教师,着手明确科研方向,与国内外专家建立联系。刚有些眉目,准备大干一场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倪维斗和一大批自己的同事一起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原是改造犯人的围垦农场去劳动改造。对此,倪维斗却乐观地说:“活了30多岁了,还没有象样地干过农活。反正是非要改造不可,也应该改造改造。”正是抱着这种乐观甚至天真的想法,倪维斗自觉地投入了艰苦的劳动。住的是十分简陋的砖房,在潮湿的泥地上垫了稻草再铺上塑料布睡,每人的地盘是80厘米宽的一条。倪维斗笑着回忆说:“以前没有挑过担子,开始挑砖上堤只能一头4块砖,40斤,我们自己开玩笑地称为“4块老表(对江西男性的俗称)”,后来能一头挑6块,就又给自己加码,8块、10块、16块,到160斤……”“双抢”时天气十分炎热,每天只睡3个小时,同伴们一个个地病倒,倪维斗却没有病,“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反而撑下来了,还撑得挺带劲儿!”乐观向上的心气儿不仅没有因为苦难消减,反而日益扎根在倪维斗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后来倪维斗又去教工农兵学员。碰上带领工厂学员去学农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教一些工人学员挑担子:“腰杆不能弯,要挺起来!工农兵学员是改造大学的主人翁,我是被改造对象,你们看看我挑担子是什么样子!”说着,他挑起担子,走起路来呼呼生风,把学员们惊呆了。乐观、开朗的倪维斗与许多工农兵学员结为好朋友,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倪维斗有时还接济生活困难的工农兵学员。
第二次青春
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倪维斗已经是46岁的人了。回首二余年的蹉跎岁月,倪维斗痛心疾首。他感到时间已经很短了,再不努力做点工作,就要辜负了这一生,也辜负了国家、人民的培养。
1978年倪维斗任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室主任,埋头一干就是6年。6年间,他带领大家始终走在我国动力事业发展的最前列。之后,他担任热能工程系、汽车工程系的系主任,继而任副校长,主管清华大学的科研与开发。令倪维斗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是,1987年,党中央邀请全国14位有突出贡献的中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到北戴河休养,倪维斗是其中之一,已83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邓小平同志勉励大家说:“对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今天没有在场的许许多多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样地,国家感谢他们,党感谢他们,人民感谢他们。”小平同志与大家合影,还和每人一一握手摄影留念。倪维斗在那里留下了一生中最珍贵、最美好的永久纪念。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悬挂在房间中央的墙面上,成为激励他前进的力量源泉。
空怀了二十余年的报国志,一朝得以实现,他的能量便象火山爆发一般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倪维斗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在人们的印象中,倪维斗总是越忙越高兴,有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活力与干劲。这些年来,他一直从事热力涡轮机系统和热动力系统动态学方面的研究,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复杂热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的先进建模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控制策略;在建立大型火电机组性能与振动远程在线监测与诊断系统中做出了重要创新成果,对先进燃气轮机的消化、吸收、应用、推广发挥了核心、组织和指导作用。
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倪维斗确确实实感到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全面的、具体的能源战略安排;宏观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比一个设备的微观传热过程的研究更为重要。因此,倪维斗在近二、三年内逐渐从能源、动力方面的微观研究过度到战略与政策的宏观研究。作为国家“攀登计划”B项目的首席专家,他指导完成了“电力系统与大型发电设备的安全、控制与仿真”重大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专家顾问组成员,他和其他专家一起完成了第一批25亿的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的战略指南、立项、评审和评估工作。
2001年,倪维斗担任了中国工程院主办的国际工程与科技大会的能源分会议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出谋划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全委会刚刚结束,朱熔基总理就仔细地听取了全委会的汇报和建议。在全委会召开以前,身为能源战略与技术组的中方组长,倪维斗也组织了煤清洁利用和分布式供电的国际研讨会,完成了联合国发展署交付的“用特许权方法加速发展风能”的报告。他认为,应利用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把传统概念上“脏”的燃料——煤,变为超清洁的能源,把动力、化工产品、液体燃料、城市煤气、供热结合起来,达到大幅度降低成本且环境友好的目的。现在,倪维斗正在国内推动以煤气化为中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他说:“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件大事推动起来,也真不虚到这个世上来一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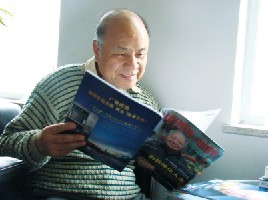 倪维斗在阅读本刊
倪维斗在阅读本刊
多条跑道实现环保能源
2006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的10位院士联名上书《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事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倪维斗是上书者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美国总统布什曾经极力鼓吹氢能经济、燃料电池,这很大成分是其出于政治考虑,目的是应对联合国《京都议定书》提出的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约规定,氢能经济在当时形成一股热潮。中国以此提出要跨越式发展,因为我们传统的石油、柴油发动机已经落于人后,而燃料电池则和发达国家都同时起步,可以跨越式前进。但这种想法是一相情愿。国家虽然为氢能研究立项并提供大量科研经费,但业内人士已经形成的共识是,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还要10年以后,而且并非汽车动力发展的唯一出路,同时并不能解决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迫在眉睫的能源问题。跨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倪维斗认为,燃料电池存在很难逾越的几大问题:一是燃料电池成本太高,比如要用其他金属替代用作燃料电池堆催化剂的贵金属铂还很难实现。国外一辆燃料电池公交车是200万美元,国内至少三四百万元人民币,轿车价格也要一半左右的成本。二是氢作为汽车动力,到现在还没有好的车载储存解决办法。现在用压缩罐是不得已而为之。氢是很轻的气体,高压氢不仅耗能、投资巨大,而且有一定的危险,容量上也装不下供汽车足够里程用的氢气。三是加氢站基础设施配置是一大难题,加氢站将来绝对不可能像现在的汽油站这样遍地开花。
在他看来,一定要理清我们的研究目的,更重要的是提高效率。要实现采用替代燃料,改善环境这个目的,燃料电池汽车还差很远,而燃料电池也不见得最终能发展起来。现在各种技术都在发展,谁跑得快谁就能赢,燃料电池只是其中的一条跑道而已,还有提高柴油机、汽油机经济性,改善其排放,甲醇、二甲醚、弱轻强混合动力、纯电动等多条跑道,中国不能一味注重单一模式发展。
呼吁应对五大挑战
在近年举行的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内蒙古经济发展论坛、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东芝节能环保技术论坛等多个场合,倪维斗都呼吁,目前正是进行煤炭现代化的好时机。倪维斗指出,要对煤进行现代化应用,要把以煤的气化和化工为龙头的多联产系统看作是应对能源挑战的战略方向。目前,这种系统绝大部分技术是成熟的,只要中国各部门(煤炭、化工、电力)打破行业界线,通力合作,在三五年内就有可能建立大型的示范多联产装置,并在2020年前后有相当数量的推广。
倪维斗说:“进入21世纪,中国能源领域面临总量需求大、液体燃料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和农村能源消耗增加五大挑战,应及早调整能源利用结构,建立完善、全面、具体的能源战略体系。”
他说,从2000年到2020年,国家规划全国GDP增长4倍,而能源消耗增长一倍。最近3年,能源需求将远远大于规划。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工业已进入重化阶段。按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能耗迅速增长阶段似不可逾越。中国石油对进口的依赖度将从40%增加为50%~60%,在替代燃料方面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走出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环境污染物的80%是由于化石能源的应用,尤其是煤的直接燃烧所引起。目前中国有30%~40%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出现酸雨现象,呼吸系统疾病不断增加。
中国已于2002年成为“京都议定书”的第37个签约国。总的来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要承担一定量、甚至大幅度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因而,从战略高度看,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认真考虑中国二氧化碳如何分阶段减排的有关战略技术和政策问题,否则的话,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999年11月,倪维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提起这件事,倪维斗非常高兴,他说:“这是对我们这个集体几十年工作的肯定,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当了院士可以延迟退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前一阵还和年轻人掰腕子、比腿劲,前几年还在新年晚会上表演红绸舞,跳得很带劲!现在我天天早上5:30起床,跑3000米,夏天游泳1000米,身体很好!”
深感到时光有限,岁月无情,虽是老骥,却志在千里。早在十多年以前,倪维斗就认识到,自己的任务远远不止坐下来推导几个方程式,发表几篇文章,培养更多的年轻人,使我国的能源科研领域后继有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任务。至今,倪维斗已经培养出博士生22名,硕士生18名,博士后5名。其中,他知道的于5年前毕业的博士于文虎与他一同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常常教导学生: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而我们最为基础的工业化还未完成。如何用信息时代的新方法去改造我们的基础工业才是最重要的。单纯的信息化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能源和环境问题在我国乃至世界永远都是热点,永远都有你们翱翔的广阔天地。倪维斗的学生说:他在教学上严谨求实,在工作中讲求科学实干,在生活中追求平淡,其人格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倪维斗说:“看到自己手底下一茬子一茬子学生成长起来,感觉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作为一位在清华学习、工作了50年的老清华人,倪维斗院士不改年轻时积极乐观的态度,虽然七十六岁高龄,不仅学术研究热情不减,努力为年轻人创造成才条件,还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扳手腕更是少逢对手。
倪维斗深爱着自己的专业。他说:“能源、动力事业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关键。燃气轮机及其系统肯定是21世纪新的能源系统的核心。因而,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每一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都将有广阔的舞台和用武之地,时势已经造就并且必将造就更多的‘英雄’。”
 邓小平接见倪维斗
邓小平接见倪维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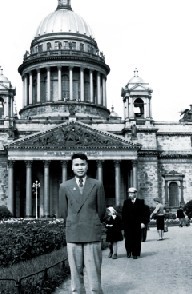 倪维斗在前苏联留学
倪维斗在前苏联留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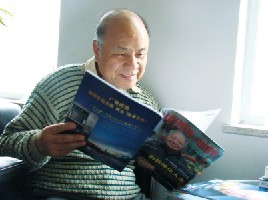 倪维斗在阅读本刊
倪维斗在阅读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