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2009-02
中国“稀土之父”
本刊记者宋 晖 刘 亮 刘 路 任 静
2009年02月01日
中国“稀土之父”
——访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徐光宪院士
 “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尽管奖是给我个人的,但应该属于整个科研团队。”
“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尽管奖是给我个人的,但应该属于整个科研团队。”2009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科技界每年一届的盛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教授的时候,年近九旬的老人满怀激情,对胡主席说出了上述这段话。人老心不老,耄耋之年的徐光宪教授,心系的仍是科研工作,仍是回报社会,仍是祖国的未来,这种精神由衷让人钦佩。
1月23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新年的脚步日益临近。作为我刊编委会副主任的徐光宪院士,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虽已是满头银丝,但精神矍铄的徐老让我们倍感亲切。谈到自己的生活,谈到自己的科研事业,徐老的脸上洋溢着微笑。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20年11月7日,徐光宪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徐宜况是一位律师。这是一个幸福的9口之家,徐光宪是7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父母亲最疼爱的孩子。徐宜况精通算数和围棋,这引起了徐光宪对数理化的兴趣,也激发了他对围棋的喜爱。在徐光宪出生的那一年,徐宜况手写刻印了《中日围棋百式》一书。这本与徐光宪同岁的棋谱,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徐老的家中。“小的时候,父亲教我下围棋,这对训练逻辑思维很有帮助。”谈到围棋,徐老拿出了已经泛黄的《中日围棋百式》,对围棋的喜爱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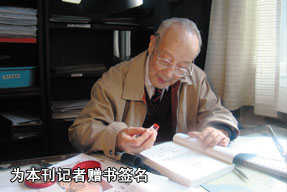 父亲去世之后,徐家家境日渐贫寒,为了能够早日参加工作养家糊口,徐光宪不得不于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浙江大学内迁,杭州高工解散,徐光宪转入宁波高工,于1939年毕业,原拟赴昆明参加叙昆(宜宾—昆明)铁路的修建工作,但路费被领班私吞,因此滞留上海。徐光宪陷入困境之中,经在上海工作的哥哥介绍,晚上去给煤球厂老板罗怀开先生家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煤球厂提供食宿和零用钱。在这段时间里,徐光宪充分利用白天及所有业余时间,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一年的学费只要10元,他还得到了奖学金,于是开始了四年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高小霞。由于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徐光宪被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聘为助教,学业和爱情的双丰收,让徐光宪感受到了幸福。
父亲去世之后,徐家家境日渐贫寒,为了能够早日参加工作养家糊口,徐光宪不得不于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浙江大学内迁,杭州高工解散,徐光宪转入宁波高工,于1939年毕业,原拟赴昆明参加叙昆(宜宾—昆明)铁路的修建工作,但路费被领班私吞,因此滞留上海。徐光宪陷入困境之中,经在上海工作的哥哥介绍,晚上去给煤球厂老板罗怀开先生家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煤球厂提供食宿和零用钱。在这段时间里,徐光宪充分利用白天及所有业余时间,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一年的学费只要10元,他还得到了奖学金,于是开始了四年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高小霞。由于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徐光宪被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聘为助教,学业和爱情的双丰收,让徐光宪感受到了幸福。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为了继续深造,1948年,徐光宪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量子化学,成绩优秀的他获得了担任学校助教的资格,拿到了1800美元的助教奖学金,这无疑让生活窘迫的徐光宪松了口气。在这里,徐光宪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唐敖庆和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侯祥麟,开始时刻关注自己祖国的命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传到哥伦比亚大学每个留学生的耳中,唐敖庆等近100多人联合起来,租下了学校旁边国际学生公寓中的室内篮球场,“根据新华社报道的五星红旗的样子,我们自己用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并邀请美国《华侨日报》主编唐明照同志(美共党员,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回国,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唐闻生的父亲)做国内形势报告,号召大家签名,给联合国发通电,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接纳新中国的代表。”谈起这段经历,徐光宪仍历历在目。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唐敖庆、徐光宪等留学生还在纽约中央公园举办了野餐聚会,并给聚会起了“胜利酒家”的名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强烈的爱国心让徐光宪深深感受到:自己一定要回去,要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那时高小霞也已到了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美国总统已提出法案,不准留美学生回到新中国,等待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后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徐光宪焦急万分,千方百计设法尽快离开美国,高小霞也毅然决定放弃再过一二年即可获得的博士学位和他一起回国。最终他们假借华侨归国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于1951年4月乘船一同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徐光宪立刻投入到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徐光宪,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从稀土资源大国到高纯单一稀土生产大国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受了“分离稀土元素中的镨和钕”的军工任务。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徐光宪担当起了这一任务的主要负责人,正式开始稀土领域的研究。
稀土元素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15个镧系元素,加上钪和钇,共17个元素的总称。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规定了35种化学元素为战略元素,其中16种元素就来自稀土。定位导航系统、手机通信、生活中的节能灯等等,都要用到少量的稀土元素;在工业中,如同人体的维生素一样,不可或缺,可见稀土元素的重要性。在世界上中国稀土储量占第一位。1992年邓小平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稀土的优势发挥出来。”1999年,江泽民也提到:“搞好稀土开发应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稀土元素的确称得上是重要的稀有金属资源。 70年代的中国稀土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外只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并没有分离的稀土氧化物。当时世界最大的稀土厂是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中国曾经考虑想买他们的技术,但要价很高,并要求稀土产品只能卖给罗地亚公司,由他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要自己研究开发,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给国家争口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老仍很激动。然而,要萃取分离镨和钕是当时国内外没有解决的难题。“萃取法”是在煤油中加入萃取剂,使它和镨、钕混合物的水溶液,通过摇晃震荡的方法将其一次次分离,最终得到纯度大于99.9%的镨和钕分离产品。但这个试验要分为三班倒,得花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而且中间的过程要经过小试、中试,最后才能投入实际生产。这一过程下来,费时费力,徐光宪开始寻求新的办法。既然萃取的过程就是确定工艺参数的过程,那能不能在理论上先将工艺参数确定,然后通过计算确定萃取剂、料液和洗涤剂的流量比例以及萃取段和洗涤段的级数呢?经过试验,他发现在几百级萃取槽中,萃取段和洗涤段的金属离子总浓度在两相之间的比值是一个常数。这就是他发现的“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串级萃取理论,和他的团队共同创建了“一步放大法”,革除了“摇漏斗”的小试和中试、扩大试验等国内外传统的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流程,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试验成功,这一方法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领先世界的!推广之后,中国的稀土行业向前跨了一大步,稀土产品的生产最终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90%,美国和日本的稀土工厂相继关闭,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也被迫减产,中国真正由稀土资源大国变为了稀土分离生产的大国,被世界稀土界称为“China Impact”(中国冲击)。
70年代的中国稀土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外只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并没有分离的稀土氧化物。当时世界最大的稀土厂是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中国曾经考虑想买他们的技术,但要价很高,并要求稀土产品只能卖给罗地亚公司,由他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要自己研究开发,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给国家争口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徐老仍很激动。然而,要萃取分离镨和钕是当时国内外没有解决的难题。“萃取法”是在煤油中加入萃取剂,使它和镨、钕混合物的水溶液,通过摇晃震荡的方法将其一次次分离,最终得到纯度大于99.9%的镨和钕分离产品。但这个试验要分为三班倒,得花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而且中间的过程要经过小试、中试,最后才能投入实际生产。这一过程下来,费时费力,徐光宪开始寻求新的办法。既然萃取的过程就是确定工艺参数的过程,那能不能在理论上先将工艺参数确定,然后通过计算确定萃取剂、料液和洗涤剂的流量比例以及萃取段和洗涤段的级数呢?经过试验,他发现在几百级萃取槽中,萃取段和洗涤段的金属离子总浓度在两相之间的比值是一个常数。这就是他发现的“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串级萃取理论,和他的团队共同创建了“一步放大法”,革除了“摇漏斗”的小试和中试、扩大试验等国内外传统的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流程,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试验成功,这一方法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领先世界的!推广之后,中国的稀土行业向前跨了一大步,稀土产品的生产最终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90%,美国和日本的稀土工厂相继关闭,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也被迫减产,中国真正由稀土资源大国变为了稀土分离生产的大国,被世界稀土界称为“China Impact”(中国冲击)。
因为稀土元素的应用很广泛,不仅稀土催化剂在石油炼制中可提高汽油成分,混合稀土还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于是中国又开始了稀土功能材料的研究,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稀土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但稀土功能材料的研究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这是全国稀土工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国内在稀土矿产的开采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稀土矿主要在内蒙古的白云鄂博主东矿,与铁矿在一起,在开采铁矿的过程中稀土的利用率只有10%,15%的稀土遭到了浪费,75%的稀土随废弃物堆放在尾矿坝。尾矿坝是一个高出地面35米的悬湖,每年还要增高0.9米,存在一定的危险,这也成了徐光宪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
优秀的人民教师
徐光宪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并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在做科研的同时,肩负起教师的责任。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他和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一起在北京举办“物质结构暑期进修班”,为期两个月,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物质结构课的师资,并在期间编著了《物质结构》一书作为教材。1988年,《物质结构》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授奖,这也成为中国教材史上化学一级学科唯一的一个特等奖。
“青少年要有时代的幸福感。”谈到国家对青少年的培养,徐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在是中国20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内需等政策,而且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青少年应该有时代的幸福感,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担落在青少年身上,要有历史使命感。人是有知识的社会动物,我们从小受父母养育和师长教导,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前人劳动的成果,所以我们成年以后,要用自己的劳动回报社会,要有社会责任感。”
“青少年要有好奇性,而且要保护他们的好奇性,这是科学创新工作的重点,特别是老师们要发掘孩子的潜力。”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徐老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徐光宪小的时候好奇心就非常强,曾经问父亲,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人的头上有多少根头发,父亲的回答是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头发数也数不清。这样的回答他并不满意,并由此开始了对天文学的关注,几十年来总是将报刊上关于天文学的新闻剪下来收藏。“好奇性是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有了动力,学习、研究才有兴趣,才能入迷。知识创新都有前因后果,万事必问为什么的好奇性,就是创新的源泉。”
小的时候,徐光宪时常生病,到中药铺拿药的时候,看到中药铺有上百个抽屉,药材被分类归置在不同的抽屉里,于是想到在头脑中也要建立抽屉,把老师教的东西分类装进去,这样就能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把老师的知识消化为自己的东西。直到现在,徐老的房间里仍放置了许多柜子,他将自己一生积攒的书籍和资料分类放置得井井有条,“这就是中药铺的抽屉。”指着这些摆满书籍和资料的柜子,徐老笑着说。如今已年近90岁,徐光宪院士仍然每天坚持工作5个小时,在做科研的同时,还在修订着1980年版的《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2008年已出上册和中册的第二版,今年将出版下册的第二版。
徐院士认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由于科技发展速度很快,知识系统的十进制分类法和英文字母分类法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于是开始整理自己十余年来收集积累的材料,并从中发现,190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500门学科,到了2000年的时候,有5000门学科,再过100年可能要有5万门学科,2050年将有20000门学科。于是他开始编著《二十一世纪知识系统的自然分类和十进制新编码法》,从中预测哪些领域能够创建新的学科。“我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在2050年前应创建至少3000门新学科。当然,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晚年的徐光宪,仍在不遗余力地忙碌着。“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着工作,睡不着啊,就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翻翻四大名著,可以帮助我睡觉。”
当记者问到徐老怎样看待科研工作时,徐光宪说出了自己对科研工作者的期待:“温家宝总理在大会发言的时候说了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科研工作者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徐光宪院士对工作的乐观态度、敬业精神以及爱国情怀,感人至深。我们相信,在老一辈科学家和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
